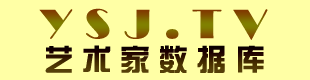闫勇,1975年生于山东陵县,自少时喜好书画,师蒙孙玉华、田瑞先生,200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,受业于范曾、杜滋龄、陈玉圃诸先生,2013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年度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。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天津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天津市第四届“十佳青年美术家”。2000年进入天津理工大学任教,曾任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绘画艺术系主任,2015年调入天津美术学院任教,副教授。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展览并获奖。
闫勇在南开上学的时候,我刚刚毕业,经常去他们班的画室玩。那时候的闫勇显得很安静,总是远离各种热闹,埋头在自己的画案上画画,桌上的废纸堆得很高,所以如果不是找好了角度,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个勤奋的年轻人。依稀记得那时候的闫勇特别喜欢临摹,也许是我去他们画室的时间比较跳跃,印象里闫勇所临摹画作的路子也比较跳跃,一会是花鸟,一会是山水,一会是人物,要么一会是范宽,一会是任伯年,一会他桌上的画册,又变成了某位当代大家。
一开始还觉得他们正赶上临摹课,后来看到他同班同学的作业,才知道不是,于是就很好奇他的写生如何,后来有机会看到他的写生,确实很有灵气,当时就觉得这个不爱说话的小师弟,有朝一日定会惊动大家。
最近看到闫勇,还是那么安静,可是画里的动静却是越来越大了。他画花鸟,也画山水,有写意,也有工笔,笔端的气力很足,线条放的很开,从画里看,作者应该有一个张扬狂狷的气质,然而我们都知道,闫勇不是这样的。那么这种反差是从何而来呢,我猜想,闫勇也应该是一个胸中经常有热浪翻滚的人,然而,他把激情全部宣泄在那些宣纸上了,他的畅想,他的激越,他的忧伤,他的不平静,他的无所谓——他所有的情绪,全都被那些宣纸一点点吸干,变成了悠远的景致与绚丽的生命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眼前的闫勇还是那么安静,甚至腼腆,甚至木讷。但是只要有他的画在那里,你就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热情的人,这就是所谓的“善变的艺术家”吧。
从他的近作中,我注意到他画里的颜色越来越有韵味了,在传统文人画中,对颜色的处理是很谨慎的,往昔的丹青高手们生怕在画中多加了颜色而破坏了那种求之不得的“荒寒之气”,然而闫勇却不怕,他有他的底气,所以他营造的山水意境既有萧瑟的诗意,也有绿意昂扬的生命感,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比起那种单调的荒寒,当是更多了一份深意。无论是《雪景寒林》还是《溪山行旅》,抑或《寒林平野》,宋代大师们似乎走的都是“苦情”路线,似乎是不悲苦,不足以动人心魄。难得的是能够在古代大师决绝的悲情中,冲撞出自己的“春花遍地”,传统水墨的藩篱也在于此,一路悲苦愤懑下去,往往会留得大名,当然,要悲愤得有意境,孤寂荒寒,疏林寒鸦,意笔廖廖,足能搏得上品,倘若是鲜花朵朵,万紫千红,阳光灿烂,一路下来,纵是有人欢喜,也总会逃不掉“流俗”的恶名。
所以,在技术操作上,无论是从语言与表现力的角度,还是从品味与立意的出发点,如何做到“笔墨荒寒而画面却饱含葱翠”堪称业界高难度问题,也就是说,在古典文人孤寂的意境中增加一些生命的率真,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水墨学术问题。我以为,任何一种学问,学术问题都应该是在总体架构中,点点滴滴的丰富与改造,那些动辄推翻前人整体框架结构的学术,也值得“学术”般的反思。
在我看来,闫勇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高难度问题,在他的山水画里我们可以看到,既有线条勾勒枯枝寒石的野逸之气,又有不张扬的石色点染下层次丰富的生命感。沉郁与欣喜,荒率与真诚,这难道不正是复杂而又真实的生活景致吗?
也许再过十年,闫勇还会这般平和,但正是这个少言少语的人,却独自走进水墨的深处,在一片无人来过的地方,构筑了自己的万千景致,也曾惊心动魄,也曾步步为营。
所以,你要明白,那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平和,那是一个艺术家在穿越激情之暇的片刻小憩。
晋陆机云:“存形莫善于画”。绘画作为一门造型艺术,形象是不可或缺的。但是只有形象,哪怕形象刻画得再逼真,也不能称其为艺术。绘画不仅要表现物象的自然生意,还应该凸显画家的性情。
汉朝王延寿在《鲁灵光殿赋》中对于“图画天地”,提出“随色象类,曲得其情”的要求,反映出绘画对形神兼备的重视。此或为南朝谢赫 “随类赋彩”、“气韵生动”理论之源。但最早的形神论多应用于人物画之中,只是到后来文人画渐炽,形神论逐渐扩展到山水、花鸟画领域。可以说中国绘画是以“传神论”为主的意象思维方式作为审美需要的,就审美本体而论,这种写意性为主的创作观一直是中国文人绘画的传统。
就花鸟画而言,花鸟画家并不只是满足于对客观花鸟形象的简单模拟,而是以自然中的景物生灵为参照,借助笔墨“托物言志,托物言情”,这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、自然物象深刻体验观察之上的一种高度凝练的情感表达,宋邓椿说。
画之为用大矣!盈天地之间者万物,悉皆含毫运思,曲尽其态。而所以能曲尽者,止一法而。一者何也?曰:传神而已矣。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。此若虚深鄙众工,谓虽曰画而非画者,盖只能传其形,不能传其神也。
可见, 人物画要求形神兼备,山水、花鸟亦皆有精神。绘画的作用就是要为天地之间的万物传神,而不单是摹写其形迹。苏轼诗云:“边鸾雀写生,赵昌花传神”,中国花鸟画一直都沿着“写生”与“传神”两个脉络分分和和地发展。“写生”并不是照搬原样,“传神”也不是空洞无物的玄谈,而是立足于自然与人息息相通之整体,对物象作出全面、本质的把握。唐代韩干画马经常写生,曾语玄宗:“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”,故其下笔如有神助,马的精神、形态甚至于马的性格毕现。五代的黄荃也很重视写生,尝自养鹰禽,以观其生态。所以他的写生珍禽图形神兼备、栩栩如生,如果没有画家长期深入的观察、写生实践,对象的神态也就很难表现的活灵活现。所以徐悲鸿先生提出写生时要“尽精微”,就是画家要善于观察抓住必要的细节进行刻画,方能“致广大”,才能使作品能感染人。“传神”不是不要形象,也是在形象确立的基础上,结合自己的主观情绪进一步挖掘物象生动的内在气质。清邹一桂在《小山画谱》中提出“活”和“脱”两字诀:
活者,生动也。用意用笔用色,一一生动,方可谓之写生。脱者,笔墨醒透,则画与纸绢离,非色墨跳脱之谓。脱仍是活意,花如欲语,禽如欲飞,石必崚嶒,树必挺拔。观者但见花鸟树石而不见纸绢,斯真脱矣,斯真画矣。
“活”、“脱”讲的即是要传写自然万物之精神。清代恽南田的花鸟作品,形色逼真,格调高雅,技法成熟而不俗腻,形象逼真然而不落甜俗。所以离开了形象,“神”也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早在战国时,荀况就在其《荀子?天论》中提出了“形具而神生”的理论,阐发了神对于形的依附关系。东晋顾恺之继而提出“以形写神”的理论,认为传神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形体的描写基础之上。形存则神存,形是神的基础,离开形,则无以谈神。遗貌取神只是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从形象和色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,对形和色大胆取舍夸张,以达到神似之目的。宋陈去非论画云:“意足不求颜色似,前身相马九方皋。”作画一如相马,要见其内在生命精神,而不可拘拘于外在之形迹。苏轼云:“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,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,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,无一点俊发,看数尺便倦。”元末明初画家王绂在《书画传习录》中解释倪云林的“不求形似”云:“不求形似者,不似之似也”。倪云林画跋原文如下:
以中每爱余画竹。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,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,枝之斜与直哉!或涂抹久之,他人视以为麻与芦,仆亦不能强辩为竹,真没奈览者何。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。
为求全其自然生意与胸中之逸气,画不工即退而求其次,并非不求似,而是随意取舍,不尽求似,这即是中国所特有的意象造型。意象不同于西方的具象与抽象,而是在自然物象与作者主体情感的交流与通融之中,使主体情感物化,客观物象我化的现象。故而绘画的形与神只在轻重取舍的程度尚有所差别,不存在绝对独尚其中一面,而尽弃另一面之举。
尤其是文人画极重“逸气”,提出鄙工取妙的形神观,如清盛大士云: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,作家之画工而未必尽妙。故与其工而不妙,不若妙而不工。但文人画之“工”是不“必求”的,而非“必不”求,只是在工与妙两相抵牾之时,更要重其内在的神质而已。然而文人绘画直抒胸臆的标榜,又往往将一部分贫学画家引向极端。由于这些画家本身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,文人绘画鄙工取意的观点便成为他们信手涂鸦的理论大旗。文人画风渐渐向大写意发展的过程中,很多画家盲目任诞狂怪,不肯在造型的基本功上下苦功夫,把“放纵”等同于“放松”,画学也渐导偏枯。这一点在传统的花鸟画中尤为突出。因为中国人物画在清代以前一直延续勾描覆染的严谨套路,虽也出现象石恪、梁楷等的减笔画家,但不在多数;由于山水画始终保持着程式的延续性,它的大写意化进程趋缓;唯独花鸟,其取材和形式都比较灵活多样,其创作的随意性也尤为突出。因而,继青藤、八大之后,又有扬州画派兴起,对大写意画风乐此不疲。但毕竟他们中大多还是比较有文化素养的支撑,其间的书卷气息犹不失可观。而今天的写意花鸟画坛,却充斥一股促黑霸气的风习。究其因,也主要是他们缺少学养和对自然形象的体察,而径接学习古代大写意的样式。本身缺少因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气韵,又不肯执着于物象的形迹,由是而形神两俱亡矣。
另外,在当代很多画家的花鸟画中,增加了一些形式构成的因素。形式构成的 “形”固然与传统形神论中所言之形有所差别。但如稍加分析就会发现,这不过是创作者对客观物象的形进行了理性的构置,或使形象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夸张变形来增添其意味性。这样的作品关键在于构成形式的合理性与创作主体精神的协调,而对于自然物象形体缺乏严谨性问题是可以不作计较的。